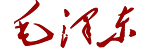透视毛泽东(下)
特设专栏2024.09.264060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人们经常低估早期教育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历程是一致的——从个人自我实现的激情到认清“阶级结构是阻碍自我实现的主要障碍”。五四运动的思想来源是欧洲的启蒙思想家,而马克思也包括其中。马克思对民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断言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与不受控制的政府一样,是对民主的威胁。马克思的其他思想,我认为并不具有很高价值。他的历史学是贫乏的;他的经济思想充满了矛盾(将绝大多数消费者的生活降低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资本主义怎么能够发展呢?),他的哲学是第三手的雅格布•伯麦Jacob Boehme)和梅斯特•艾科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秘主义(当我读到黑格尔时,立刻就想到了Boehme)。
从哲学角度来看,毛泽东接受了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意识概念。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共同创造新认识的方法。在其它地方有人会将这种方法称为“参与型研究”。毛泽东的认识论,将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挂钩,但是你也可以追溯到杜威那里,因为毛泽东强调反复试错的过程,这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毛泽东眼里,群众路线与他的认识论是紧密相联的,这不仅表现为上述关于群众路线的讨论中特别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且还表现在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的结尾一段极其相似的文字中: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除了五四运动引入的欧洲启蒙思想,中国也有自己的启蒙思想。王阳明关于“理”的学说,推崇“知行合一”。王夫之反对照搬古代的典章制度阻碍今天的发展。顾炎武认为,中国历史上当地方拥有自治权时国势趋强,而当君主专权的时候,国势趋弱。黄宗羲认为,仕作为儒家价值的看护人,应该代表人民而不是君主的利益。康有为认为,儒仕应该避免空谈,努力实践,追求尽可能接近自己的理想,政治因此成了一门关于可能性的艺术。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肯定受到了东西方启蒙思想的洗礼。
尽管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毛泽东后来几乎从未源引西方“理想主义”作者或者儒家学者,但是这些人确实对毛泽东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有深刻的影响。除了格林的认识论以外。约翰杜威特别值得提及。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的整体论之间的对比经常被过度引申,杜威相信,人类所能了解的真理只能来自对可预测变化的观察,人类通过对事物的改变来学习。马克思认为,认识来自于革命性变革过程中的行动。陈独秀将两者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是杜威将陈独秀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很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务实的行动不能没有目的,而目的基于价值观,这些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认识论里发现回声。
在格林和杜威之后的第三个西方思想源头,是托马斯•克库伯,他的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书。克库伯谈到了,圣西门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文/傅立叶的公社社会主义的矛盾分歧,介绍了欧文关于人类的本性,可以通过社会变改得到完善,就像欧文在自己的磨房工厂里进行的社会实践,改造了在那里工作的、原本赤贫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克库伯还认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应该由实践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不同的国民特质,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相对应。
应该注意,在毛泽东读到克库伯的时候,斯大林主义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克库伯在中国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1982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还听说他的书再版的消息。当然,毛泽东的早期教育,对其后来思想的影响的研究,只能是一种猜测,我们所知的包括毛泽东在长沙图书馆的自学,还有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是杨昌济送给毛泽东一本由江亢虎翻译的克库伯,我们还知道,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可能读到的书籍,以及他在一篇文章里对杜威思想的热烈回应。
毛泽东将很多思想融会贯通:意识动机;通过试错法,找到可预测的现象,从而形成知识达至真理;社会主义提供了,在国家集权控制和统一物质分配的共产主义形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地方自治而非中央集权,是决定中国国力的基本因素;个人的自我完善,只能通过与他人的互助合作达到;僵化的制度阻碍发展;以什么样工具创造社会主义,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智慧归根结底来自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府的基础是共识;一个人意志力的大小决定于他自尊的程度;社会主义依国情与传统的差异而有所差别。所有以上这些观点,要么有毛泽东的原话为证,要么可以由他的行动中得出。
毛泽东最初在长沙的政治活动,让他不得不相信,只有武力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湖南的省议会,与中国的国家议会都是徒有其表。所谓民主制度,有时确能窒息社会改良的真正努力,这为1945年以后许多国家的情况所证明。毛泽东的优先选择,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共同反抗压迫。压迫与反压迫,构成了历史的主线。我们要问只是:毛泽东最终是坚持了这个信念还是背叛了它。(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6年中,毛泽东在党内一直是代表农民的,他是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领导人。1927年他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报告,同年蒋介石的政变迫使毛泽东进入江西农村。1934年,红军被迫退出江西开始长征,并一路打到陕西。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着一个国中国——一个农民的中国。在国民党人眼中,有两个共产党,一个陕西党一个上海党。有一点我无法证实但仍然相信:当刘少奇想到中国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沿海的发达地区,而毛泽东想到中国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内陆的不发达地区。
在边区的时候,毛泽东初次开始处理经济问题。边区必须加强经济来抵抗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封锁。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希望发展政府所有的工业和完全集体化的农业。毛泽东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采取了共助组和工商合作社的道路。
施拉姆(Stuart Schram)不相信边区经济与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有联系,因为边区时期不存在国有经济。施拉姆对毛泽东研究贡献良多,但这一点我无法不反对他。在边区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毛泽东称赞非政府经营的工业合作社,并且将延南合作社树为榜样。(这一部分在再版时被删除了)。我一直相信,工业合作社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合作以村为基本单位,充分利用劳动力,将所得收入迅速投入再生产,从而积累资本和技术。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农民,而领头的往往是从城里来的年轻技工。工业合作社的组织是“地方管理,中央监督”,管理是民主的,有的时候是超民主的。由于没有配套企业,他们不得不什么都做。在边区现有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收入,支撑了村里医疗和教育的开支。据斯诺报道,合作社充当了全村甚至跨村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角色。边区时期,毛泽东推崇的工业合作社模式,与20年后人民公社之间深刻的相似性是不能被忽视的。
边区的另外一些合作社,由边区政府或军队组织管理,提供技术和资金。它们就像大跃进时期国有经济部门,同时也可以视其为公社制度的先声。
从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学徒计划和传教士,在上海郊区创立的自助合作社,经过工业合作社,再经过建立在使生产的多样化的特定计划(如《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述)之上的边区合作,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条线索是连贯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新高潮中,将人民公社定义为更大区域内的合作,目的是提高分工和生产多样化。为什么要否定这种连贯性的证据呢?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刚刚过半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新高潮一书里指出了,个体农民要走合作化道路的方向。从始至终,毛泽东强调的是,通过激发农民的创造性和利用农村的资源,来制定生产计划、增加合作社社员的收入。新高潮的思想立足于缺乏资本的现实,用集体的组织手段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劳力投入获得后续的投资,积累技术迈向人民公社。相当可信的数字显示,农民的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在原来基础上都有提高。在土改之后,最富有的农民拥有的土地一般是最穷的农民的两倍,但是,富民70%到75%的收入要用于养家,由于富裕农民往往家庭规模更大,所以他们在基本生活保障线以上的收入不到贫民的两倍。在保证基本生活需要之后,任何小的生产效率提高都可以带来可支配收入的显著增加。这使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加入到集体中来,进行分工合作。
新高潮一书中给出的第一个例子是,农业合作社的党支书王国番,在村里富家不愿意入社的情况下,带领贫民进山拾柴卖钱。这是在农闲时做的,所以几乎没有机会成本,等他们攒够了钱就开始投资,合作社越搞越大。两年以内中农们看到有利可图都入了社。这个例子也许是虚构的,但它的逻辑是可信的。
这说明,毛泽东本意是要用渐进的办法来搞合作农业,但是后来他急于推进,合作化遭遇了富民的抵触。据毛泽东自己说,在这一过程中有80000人被处决,平均每50个村庄有8人,这些人是谁又是因为什么被杀,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但是,必须说明的是,直到1950年代中期,前国民党的支持者,依然在很多地方进行暗中破坏,那些被处决的人当中应该包括了这部分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合作社并没有创造很多非农业的工作岗位。因此大跃进就成了第二次机会。在出版后三个月,毛泽东就在讲话里提出中央要放权,调动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这实际上用市场手段减弱中央统配,由部门间的准市场互利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权威阐述。
接下来是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这是党第一次邀请公开的批评,批评本是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但是全国规模的大批评还从未有过。反右被认为是给异见分子挖的陷阱。是毛泽东的引敌深入的策略。但是,实际上毛泽东从未同意过对右派进行惩罚。(如果他支持那么惩罚,为什么又宴请一批知名的右派并公开与他们的合影)。事实上,毛泽东反复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不接受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要耐心教育。
在中,毛泽东对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提出了批评,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细致区分。对于那些拒不接受革命思想的人,毛泽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时间来解决他们。而对于人民内部的意见和利益分歧,则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
有人持有反右破坏了党内共识的观点并不令人吃惊。1950年代初,毛泽东就发动了“反对官僚主义和长官意志”的运动,他对官老爷是深恶痛绝的。文革中,红卫兵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成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我毫不怀疑,毛泽东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大跃进不只是把群众路线当作政治时尚,而是把群众路线当作是,最有效最民主的社会变革的工具。人民参与设计完成这个变革,提供制度雏形,党来加工完善。在经济领域,权力下放,中央官僚机构无权下命令,而只能对地方的动议进行反应。
麦考法尔在他的一书中说,文革脱胎于大跨进。他的考察的历史阶段很成问题。他从大跃进的中期入手,止于文革之初,这样就忽略了大跃进本身的起源和文革的后果。这样对大跃进和文革的认识都难以成立。因为大跃进初期的成功被排除了,而正是这一成功所造成的过分乐观,导致了后来灾难性的政策执行扭曲。而且,他的书根本没有触及文革开始后得以复活的大跃进战略,这一次相对克制的政策取得了成功。麦考法尔绕过了根本的经济战略问题,营造出从1958到1976年的全部运动不过是意识形态之争的假象。在书中作者引述了共产党领导层的多次讨论,在一次争论中毛泽东插话道:“公社必须尽可能多产商品、才能多赢利。”对此,麦考法尔没有评论。而这一完全非意识形态的言论反映出无论党内辩论使用的是多少深奥的政治语言,问题仍然是实际的经济问题。
文化革命被很多人视为由文化问题触发,其实经济问题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主张同彭真、刘少奇的不同。毛泽东让村庄购买拥有自己的拖拉机,他是在1958年提出这一建议的。文革后又由林彪重提。但是彭真在传达时,故意将毛泽东对苏联拖拉机站政策的批评砍掉,从而否决了这些建议。根据红卫兵的批判材料,刘少奇想搞苏式拖拉机站。彭真因为支持刘少奇,再加上庇护攻击大跃进的杂文作家而被免职。
文革开始时受到攻击的作家们都曾谴责过大跃进。这些作家受到对大跃进的失败感到心灰意冷的领导人的保护。在当时的中国,所有作家都是为自己的庇护人服务的。说这些受到攻击的作家是公正独立的根本上是荒唐的。而在那个时期,没有任何庇护人或者作家能够发表有利于毛泽东的战略的论据。
毛泽东的继承之争开始后,言论出版成为重要的较力场,当时,右派的解冻就意味着对左派的封口。在西方评论家那里,这被视为是意识形态化的毛泽东与务实的亲自由领导人之间的斗争。而正是这些所谓的务实领导人,在此之前一直被称为和毛泽东一样的共产主义暴徒。反右的时候,邓小平在哪里?他是反右运动的领导,是毛泽东对反右感到痛惜并反对扩大化。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又在哪里?他在全国各地巡视,对所有的浮夸和反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当毛泽东要求中国的年轻人批评他们的领导的时候,刘少奇在哪里?他在组织党的工作组去控制学生。毛泽东的反对者提出的“利伯曼”式的改革方案,在一度实行之后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成果。而毛泽东的社队办企业在1970年代复兴,一直到1979年邓小平上台发展的如何?他们贡献了中国一半的工业增加值。使中国农民的收入达到了中等国家的水平,中国人的储蓄是邓小平开始他的经济改革的本钱。
利用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来发展农村,可能是绝大多数穷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最佳选择,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才能办到,但是,是毛泽东第一个发现了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不错的墓志铭。
关于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潜力,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个水土保持的项目,在北京以西100英里的一个村庄。山区坡地经常受到洪水的侵扰,当时的粮食作物是水稻。村民们在山坡上种下了50万棵树,这些树的树叶可以作为饲料,树窝能储留雨水。坡上的小垅就像是小型水库,农民手工清理淤泥保持水土不流失。这种办法涵养了水源同时发展了牲畜生产。使农民有钱购买自己的第一台拖拉机。
第二个例子,山东栖霞县的一个社办工厂。这个厂最初是从组织家庭妇女缝制手套开始的,在大跃进中他们除了手套还生产其它纺织品。因为这个厂太小,才得以从刘少奇对社队办工厂的扫荡中幸存下来。从1970年开始,它扩大生活。当尼龙出现后,它转向了生产波纹尼龙布。当1982年我去这个厂考查时,他们生产的尼龙轧纹波机已经行销全中国了。
1982年,我得到去中国考察的机会。我计划在中国的山东,江苏,四川的三个村庄里呆了三个月,这三个村庄的经济条件分别是很好,中等偏上和很差。北京同意了我的计划。很好的那个在江苏无锡,中等偏上的村子在山东的栖霞县,很差的那个在四川西部的洪雅。在这三个村子里,我学到的东西比我在北京学到的多得多。在山东,我和农村干部一杯下肚,就不再有什么不能谈的了。这让我不但了解到村办企业的潜力和问题,也看到了它对农民的心理影响。村办企业让农民有了新的眼光,他们变得自信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农民自我意识革命的开始。
农民对这种发展方向的肯定,使我相信这是通向新的公民社会的开始。当时,全中国有大约200万个社队办企业参与市场活动。小企业越多,市场就越复杂,大量的企业和复杂的市场,让行政干预变得更困难,市场中的谈判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商业往来取代了党内的上下级关系。基级干部开始认同自己在社队企业里的角色,这类似于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提出的,市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侵蚀。一个新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兴起,它当然被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痛恨。毛泽东肯定是意识到了,经济权力下放对在市场上活动的小企业的政治影响。他就是想给在生产一线的人发挥创造性的空间。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悖论:中央计划的成功,只能来自于基层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毛泽东认为,苏联式中央集权控制,只能在被控制者那里引起阻碍生产的反制反应。我在中国农村的田野和社队工厂里看到、听到的是,积极务实的行动和期望,中国的农民正是变成活跃的国家公民。我不是在理想化社队派企业,很多企业最终不成功,很多依赖于村落里的补贴,还没有产生效益。有不小的浪费,不少对环境还有不良影响。甚至滋生腐败。但是我们不能用自己社会的理想样本,来评判别人的现实。西方的小型企业也受到几乎同样问题的困扰。实际上,西方小企业的失败率甚至要高于中国。
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从毛泽东开始的。在文革中他说造反有理,在文革陷入混乱以后,红卫兵学到的第二课,就是没有制度和程序的保障民主就是无法存活。因此在李一哲大字报里,作者认为毛泽东推动的民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需要建立相适应的民主制度。1976年陈尔晋上书毛泽东,他说由于需要用暴力来推翻旧的剥削阶级,革命必然创造一个威权政府,这在革命后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因此需要二次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应该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经过红色资产阶级进入民主社会主义。陈的主张,实际上成了民主墙运动的基调。之后,源自红卫兵的这支追求中国民主的力量,完全不同于北京的那些要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求推动广泛的人民民主运动。六四的结局,与这一支民主力量的发展引起邓小平的警惕,有重大关系。由昔日红卫兵推动的民主运动,在90年代以后仍在继续,直到J Z M收回了他对多元政治的有限支持, 监禁了王有才, 徐文立和秦永敏等人为止。
寻找毛泽东思想与行动中的积极因素,并不是要否认他是一个独裁者。尽管毛泽东一直反对滥用刑罚和处决, 但在他相信必须这样做时, 并不手软。为了保护革命事业, 革命的敌人必须付出代价。在我看来, 他更像是奥立弗•克伦威尔—— 本质上倾向民主, 但是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大权独揽, 他这么做正是为了捍卫民主的价值, 因为他的将军们既不理解也帮不了他。
作者简介:杰克•格雷(Jack Gray)为英国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文章译自“Mao in Perspective”(China Quarterly,2006 Sep.),作者Jack Gray为英国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其代表作为《造反与革命:1800年至2000年的中国》,他本想在退休后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政治传记,但直至他去世都没有实现这一计划。为纪念Jack Gray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于2006年秋季发表了一组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文章,包括Jack Gray的《透视毛泽东》及若干回应文章。《透视毛泽东》是由《中国季刊》根据Jack Gray关于毛泽东的手稿整理而得。
本文转载自互联网,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相关推荐